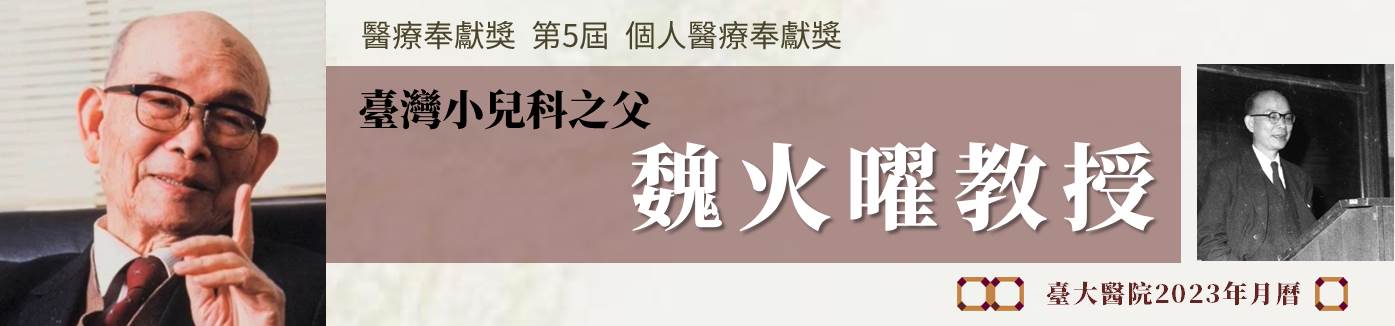
做良醫,不要做名醫。
-魏火曜教授,臺灣小兒科之父
文章轉載自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
魏火曜小檔案
魏火曜,1907年生,臺北人,出生書香家庭,排行長子,家境清寒。在父親魏清德鼓勵下,隻身負笈東瀛,入東京帝國大學苦讀四年畢業,並留任帝大擔任五年無薪助手,直至1942年榮獲醫學博士。之後,曾返臺及至廈門服務。並與基隆世家顏國年之女、顏碧霞女士於1934年成婚。1946年任臺大小兒科主任,兩年後升任臺大醫院院長,至1953年,接掌臺大醫學院院長,任期長達十九年。1972年,卸下院長職務,轉任臺灣大學教務長七年,其間,197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,1979年辦理退休。
退休後,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,但仍以社會公正人士代,出任許多公益團體理事、監事、委,並任中華血液基金會董事長,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等。最後因罹患大腸癌,於1995年2月6日下午病逝其長子魏達成家中,享年八十九歲。
被醫界尊為「大家長」的魏教授,一生集學術清譽、社會聲望於一身;他對國內醫學教育、臨床制、社會公益事業的貢獻,很少人能與之相提並論。這一切,固然得自於他所生長的時代,但他終能不負時代託付,奠基創新;尤其是他自奉歛樸、熱心公益、淡泊名利的行事風格,更讓人緬懷他所代表的一個逐漸遠去的年代。
過去一提到醫界大老代表,大家閉眼也會毫不遲疑地說出:「魏老!」是的,魏教授曾是醫界、甚至是整個社會公認的醫界代,他不僅是臺大醫學院的前院長,更是醫界的大家長,當然也有人以也曾在醫界叱吒一時的「魏家班」掌舵者來稱呼他。中央研究院曾為這位見證臺灣近代發展的國寶級人物出過口述歷史,所有醫學教育的擘畫,都會尊重他的意見;而社會公正人士、公益活動的代言,也少不了他。他為人謙沖,卻四處活躍,一生友朋、弟子無數,獲得的尊崇、名位也無數;但是,醫療奉獻獎舉辦到第四屆時,他一直只是默默坐在頒獎典禮看臺上,真誠地為每一位得主鼓掌、致敬。直到1995年2月8日,這位醫界大家長辭世了,第五屆的醫療奉獎才頒了「特殊貢獻獎」給他。
這分遲來的榮譽,其實,對生前已集學術清礜、杏林威信、社會聲望於一身的魏老而言,不過是眾多榮耀事蹟外,再添一筆罷了;從臺下到臺上,即使魏老未能親自領獎,但國人不會忘記他一生於醫學教育、醫院行政及社會工作奠基、創新所立下的功業,令人對他有無限的感念。
衡諸國內醫界,像魏老這樣,做了國立醫學院院長、兩所醫學院院長,且醫學院院長任期長達十九年的經歷,可謂空前絕後。但是,獎勵他方特殊貢獻,絕非因為他曾頂著這麼多榮耀的頭銜,而是,在這些成就背後,一方面它代表了「時代造英雄」;魏老生在一個艱困的時代,本土醫學還未發芽,是魏老以「老園丁」自居,蓽路藍縷,埋首於醫學園地的整地、施肥、育種工作;他不僅在戰後的匱乏時,一點一滴地建立了國內小兒科發展的規模,對於當殘破不堪的臺大,也以勇於改革的精神,大刀闊斧地革新,始無負於時代的託負。
另一方面,也由於他無私的付出,全心的投入,接掌臺大醫學院期間,讓臺灣醫學教育自日式度脫胎換骨,大力培植人才,聘請美藉顧問協助革新,改善教學設備,提升教學品質。在其手下,並曾陸續增設了藥學、護理、醫學技術、復建醫學等科系,設立了八個研究所,三個博士研究班,臺大醫學院今天能執醫界之牛耳,並享名國際領域,泰半奠基於魏老在任內的勤於耕耘,勇於開創。由此可見,他也是「造時勢」的真英雄。
學醫為救人 選擇由新生命開始
1907年,魏教授出生於新竹北門的清寒家庭,排行老大,下有一弟一妹。由於身處日據時代,在當地「國語學校」接受日文教育,由在小學任教的父親教習漢文和算術。七歲舉家遷居臺北萬華,進「老松公學校」,即今老松國小前身。畢業後,考進「臺北高等學校預科」完成七年中學教育。
由於當時公共衛生落後,醫療資源缺乏,父親希望他不僅能有一技之長,換得溫飽,更盼他能行醫,換救他人性,不計艱難,送他及弟弟魏炳炎先後赴日習醫,因而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。
1930年,二十三歲的魏火曜隻身來到日本,但第一次投考帝大醫科不幸落榜,隔年才考上,開始在艱困的環境下學習,四年後自醫科畢業,他留在帝大附設醫院當了五年無薪助手 ,一方面繼續進修,終於在1945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。
基於現實考量,魏火曜選擇小兒科為終身職志,因為小兒科容易開業,對經濟狀況不佳的他,最為實際;而且,他弟弟魏炳炎學的是婦產科,弟弟接生的小孩,正可由他照顧。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,當時臺灣環境衛生落後,傳染病猖獗,許多小孩來不及長大,便失去生命,「學醫既然是為了救人,就由新生命開始吧!」
臺灣光復後,魏火曜應當時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博士邀請,回國擔任小兒科教授,並兼臺大第二附屬醫院(即今日中興醫院)的小兒科主任,從戰後的貧窮匱乏中,一點一滴建立起臺大小兒科的規模。當時醫院缺水,他常須和同仁從一樓提水上四樓,儀器缺乏,便自己設計創新,終使小兒科的情況改善。
為求改革 挺身面對壓力及恐嚇
兩年後,他升任臺大院長,開始更艱苦的建設。戰禍中嚴重毀損的臺大醫院房舍,亟待修復;時任校長傅斯年則要求臺大醫院的行政組織革新,力求現代化;再加上社會的動盪不安,醫病間的摩擦、同仁間的爭執不斷;魏火曜不僅承受來自各方壓力,其間更曾多次遭人以槍械恐嚇、威脅。
1953年,魏火曜轉任臺大醫學院院長,展開長達十九年的醫學教育工作,而他建設的腳步並未停歇,只是地點由醫院轉至醫學院。當時他利用美援,延聘國外顧問到校協助,並選送教師赴美進修,積極改善教學設備和方法。
為提升臨床教學的品質,他協助醫院加強護理部門作業、修建開刀房、增添檢驗儀器、增設嬰兒室、急診處、病歷室,不僅因此改善診斷和治療的水準,也改進了臨床教學方法,提升了患者的待遇。
為因應醫療人力缺乏的困境,魏火曜並陸續增設了牙醫、藥學、護理、醫事技術、復健醫學等科系;而在美援逐漸減少後,他仍持續爭取經費和設備,興建各種科系研究室、館,並先後設立八個研究所、三個博士班。臺大醫學院所以能成為國內執牛耳的醫學園地,魏火曜任內奠下的基礎,功不可沒。
魏教授不僅在醫療行政和教育上,扮演了稱職的角色,在他的專業領域小兒科,表現也未令人失望。雖然忙於行政工作,不得不減少看診的時間,但他一心致力於提升國內小兒科醫療水準,成立小兒科醫學會,讓國內醫師的進修制度化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三十多年前,小兒麻痺仍在臺灣肆虐,平均每年有近千名兒童因此喪生,成殘者更難以計數。當時沙賓口服疫苗已在國外普遍使,魏教授便以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的身份,極力建議衛生單位進口。經其奔走努力,國內終於1966年採購沙賓疫苗,免費提供兒童接種,解除小兒麻痺的威脅。這也是魏老一生中最引以為傲的事蹟。
帶著「誠」先生 接掌高醫
較不為人知的是,魏老也曾當過高雄醫學院的院長。當時高醫因內部問題,鬧得不可開交,魏教授奉命南下,接任院長一年餘。當時人人以為,他一到高醫,必然會大量安插人馬,但魏老說:「我只帶一個『誠』先生來!」因而引為杏林佳話,許多人也因此對他的任事風格印象深刻。在投身醫學教育的三十三年間,魏火曜對國內的教育貢獻厥偉,並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即使在其退休後,仍接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,不改對國內醫學教多所建言的習慣。後來,由於教育部決策常常與其建言反其道而行,他才為堅持原則而請辭。
魏老此一擇善固執的立場,不但成為政府各項醫療決策的重要諮商對,相關醫療公益活動更也少不了他;總計他曾參加十數個醫學會,任二十餘個公益團體的理事長、董事長,及各項公益性無給職的頭銜。直到去世前,還以八十九歲的高齡,任中華血液基金會董事長,除臥病期間,每天無分晴雨,準時到捐血中心上班。國內捐血事業能擺脫「血牛」買責賣血液的惡劣形象,步向無償、現代化的管理,亦為魏老一生的重要事功。
已故民俗學者林衡道,由於魏、林兩家早年都以詩禮傳家,在年輕時代即和魏老已熟識。林衡道曾稱許魏老行事謹慎、守法有節,且生活極為檢僕,他印象最深刻的是,魏老從小非常孝順,即使赴日取得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,歸國後在臺大醫學院任職,每個月薪資都文風不動地交給父親,而後再由父親手中領取少許的生活費,其孝行向為人所傳頌。
與魏教授也有數十年同事之誼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彭明聰,猶憶起當年魏教授任臺大醫學院院長及教務長之際,最愛惜物力,冷氣機在那時仍屬「奢侈品」,他不願購置,認為吹冷氣代表貪圖享受。但同仁有感於院長室常有外賓造訪,總不能讓外賓在大熱天裡揮汗如雨,「要不是趁魏老出國開會,我代理院長時,私下作主裝冷氣,他說什麼也不同意。」
和魏老同事四十多,當初胼手胝足共同建設臺大小兒科的小兒科教授陳炯霖,則透露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往事。當時省衛生處長許子秋剛上任,邀請魏教授、軍醫署長、農復會衛生組長共同到日月澤涵碧樓請益醫療衛生興革之道。當陪客的他,頭一次看到五十多歲魏火曜,為了當年醫學院畢業生鮮少願下鄉服務,竟然激動得掉下淚來。
看病送奶粉、掏腰包 樂在其中
魏教授始終主張,身為醫學生,道德教育應與醫術並重,但在醫學院裡開醫學倫理教育課程,他卻說:「起不了什麼作用!」因為,如果醫師、教授們收紅包,不重身教,這些將來的醫師也好不到那裡!
他常要求學生「要作良醫,不作名醫」,名醫光是應酬、看別人指定要看的病,時間都不夠,又怎能好好照顧病患?但世人都追求名醫;對醫學生來說,懸壺不忘名利,多數來自家裡的壓力,他也不例外。
他剛回國從事小兒科醫師時,看的盡是營養不良的小孩,他常感慨;自己費心診治的效果,遠不及他們對一罐奶粉的需求,因此,他常常在看病後,還讓病人帶一罐奶粉回家。魏老雖然「虧空」累累,但他心中卻有無上的滿足。
他最後離開臨床,走上行政,也並非厭倦了行醫,而是發現大環境的需要。他說,抗戰勝利後,光是臺大醫院這棟建築物有數千塊玻璃待補,如果他未能投入做環境的改善,怎可能給醫者較完善的行醫環境?
臺大小兒科教授呂鴻基說,魏教授做事認真,對學生論文修改仔細,說的不,但是字字鞭辟入裡,從不擺架子。他雖然從事行政工作,卻熱愛臨床,即使退休後,每天臺大醫院早上八點的小兒科早會,他準時參加,直到去世前,因健康關係才叫停。這段歷史已成為教授激勵晚輩最好的「身教」。
臺大小兒科教授李雲說,許多人當醫師是為賺錢,魏教授卻不把錢放在心上,從不曾在外兼差開業,同一套衣服穿了許多年,沒有新衣替換,家中擺飾、飲食,更是簡單得令人難以想像。他並捐出多筆土地,以發展公共事業,魏老夫人雖出身世家,也是留日高材生,但半世紀以來,一直從事醫療有關的慈善事業,對魏老捐錢、捐地從未有微詞;對他們而言,生命就是無止境的付出。
如此嚴謹的魏老,如果你以為他是正經八百的老學究,那就錯了!魏老其實也是最浪漫的老派人士。他愛藝術,閒來也提畫筆,彩繪記憶中美麗的風;他愛不言不語、亙古不變的石頭,不經意地收藏,細細地品玩,卻打趣說:「這些都是不花錢的玩意兒!」
魏老常常換辦公室,但是在每個他待過的辦公室,總掛著幾幅淡雅的風景素描,常有人問他:「這是那位行家的手筆?」這時,他會笑得像孩子似的,說:「亂塗的!」
魏老喜愛美術是從童年開始就常信筆塗鴉,中學時代還曾受一位日籍老師影響,鼓勵他多畫,但他說,由於家貧買不起照相機,「只有提筆用畫的囉!」
魏老生肖屬猴,他蒐集所有關於猴子造型的玩偶、泥雕、銅塑、繪畫等,許多學生知道了,遇有猴玩意,總不忘送他,他到底蒐藏多少猴子?魏老說,自己也算不清了,「是有不少,但是和蒐集的石頭一樣,都是不值錢的,喜歡而已。」他淡淡地說。蒐藏於他,不是為了擁有,而是對生命的另一種禮讚。魏老喜愛美術是從童年開始就常信筆塗鴉,中學時代還曾受一位日籍老師影響,鼓勵他多畫,但他說,由於家貧買不起照相機,「只有提筆用畫的囉!」
自比「做田人」 一生耕耘醫療與教育土壤
魏老生性豁達,在他晚年長子臺大外科的「名刀」魏達成教授,因中風倒在手術臺上,別人擔心他承受不住老來愛子病倒的打擊,但魏老那段時間總是一語不發,每天準時地出現在開刀房,主持醫療小組會議;他的堅強,愈發讓人心生不忍。
魏老八十四歲時,首度發現罹有大腸癌,即由當時的臺大外科名譽教授許書劍為他切除,隔年,再發現直腸尾再出現另一處癌蹤,他也二話不說,勇敢地再進手術室。不過,當1994年底,即去世前一年,臺大證實癌細胞始終未離他身,甚至造成全身性轉移時,魏老處理自己的健康,依然守持一貫的風格,腦筋清楚,不拖泥帶水。他說他在第一次開刀時就偷偷許願,能再活三年,就夠本了。果然,老天沒讓他失望。最後那段就醫期間,他對自己的病情最清楚,一度不願再住院,也拒絕進一步化學治療,最後在家人陪伴下,安詳地於長子魏達成家中辭世。
魏老形容自己有如「做田人」,把生命毫不保留花在醫療與教育土壤上,做犁、整地、播種的工作,他未曾想過要收割。但展望半世紀以來,「魏火曜」這個名字已成為臺灣近代史重要的指標,他不僅見證了臺灣醫學發展從百廢待舉到繁榮的過程,奠定了基礎醫學的根基,確立了臨床制度的完整,一步一腳印,我們實難忘懷這位偉大醫學教育者留給我們豐盛的園地。我們緬懷魏老,不止告別了一位歷史的老人,也在向一個堅持儒醫精神,要求行醫淑世的美好時代告別!

1960年小兒科新病房落成,魏火曜教授回診實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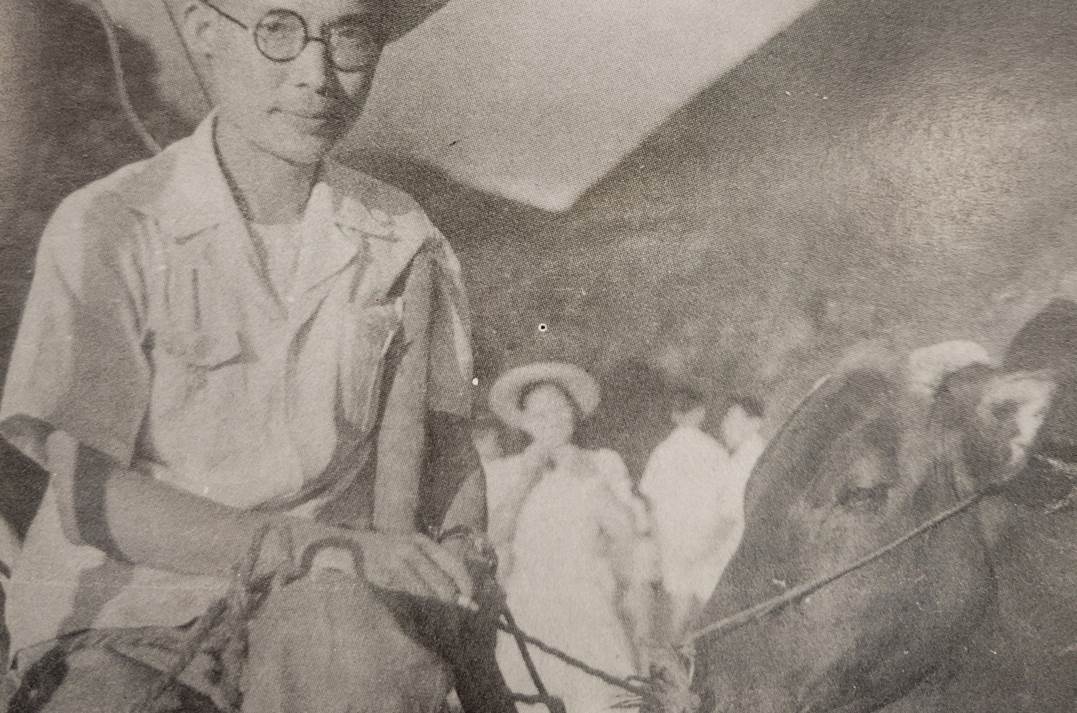
1947年魏火曜教授兼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與同仁烏來郊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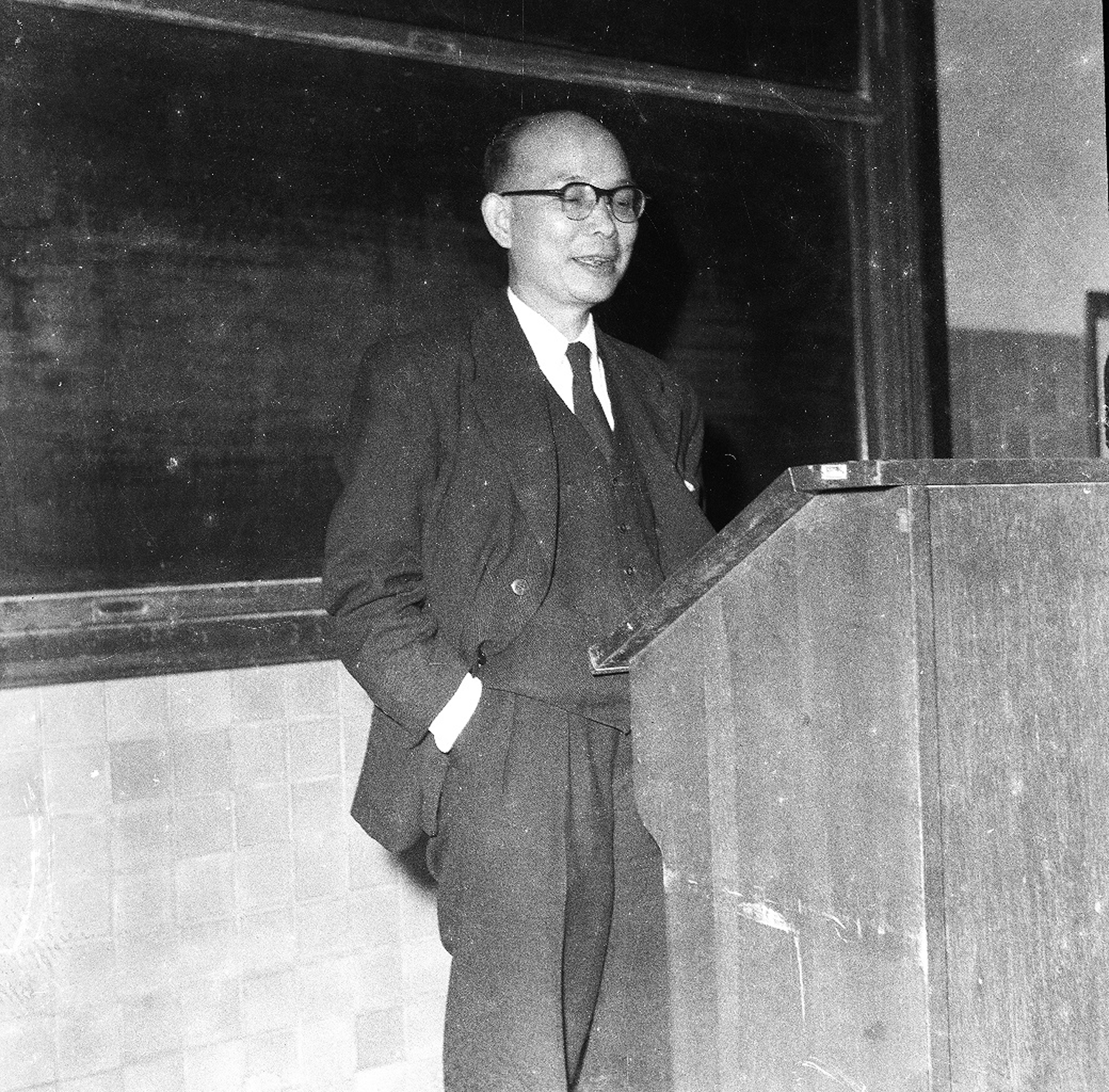
1953年 院長交接典禮由魏火曜移交高天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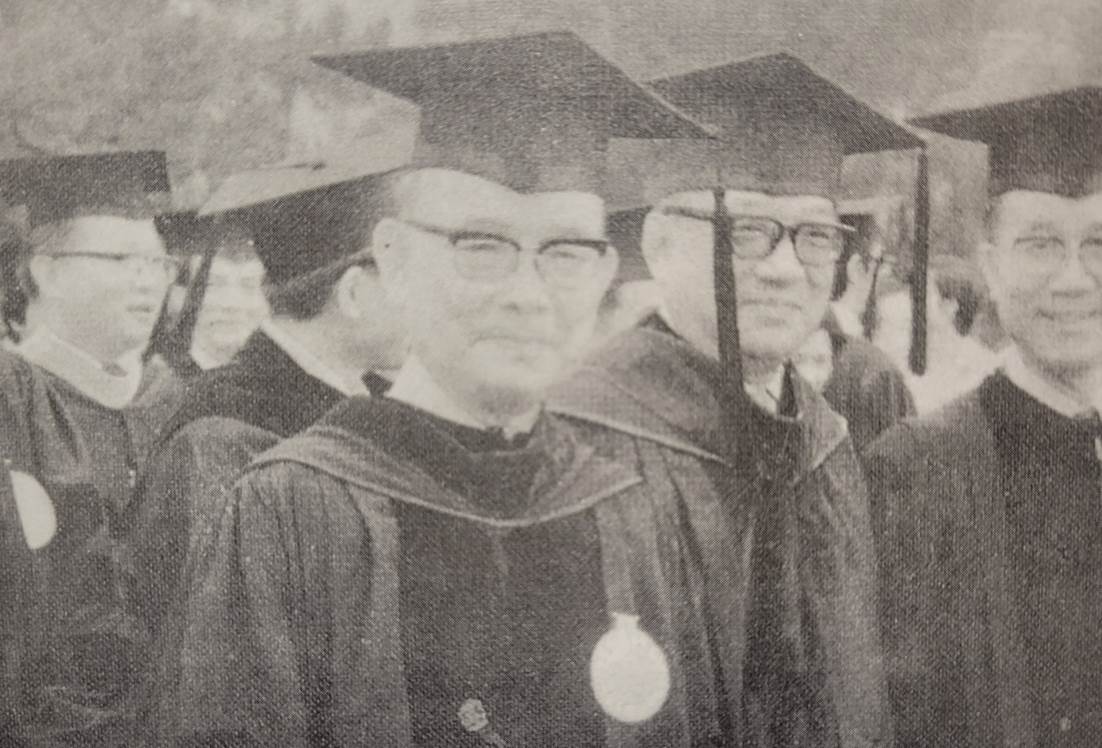
1979年魏火曜教授出席臺大畢業典禮
資料來源:
-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-個人醫療奉獻獎 魏火曜(http://www.hwe.org.tw/Html/WinnersPage?Id=172)
-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/ 熊秉眞,江東亮訪問 ; 鄭麗榕記錄
- 魏火曜教授生平文物展(https://www.lib.ntu.edu.tw/events/2011_wei_huo-yao/virtue.html)
影音資料:
- 被譽為台灣小兒科之父的魏火曜教授(一)【民視台灣學堂】這些人這些事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MWuFKxxybA)
更多生命影響生命的故事...(連結)
